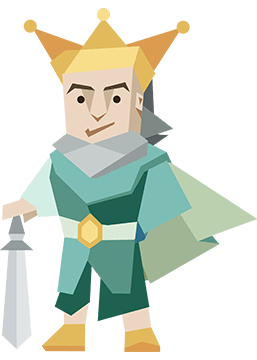剧情家
剧情家为您提供电视剧分集剧情介绍,是您看剧情的必备网站
- 导演:简川訸 编辑:兰小龙
- 类型:战争
- 地区:中国内地 年份:2016
好家伙三集联播
第1集:芦焱亡命天涯得“种子” 屠系若水共党三方秘会分集剧情介绍
一九二七年,北伐大捷,一个期盼了近百年的少年中国似乎近在眼前。四月十二日,国民党激进派联合帮派势力,向红色阵营发动袭击,史称“四一二政变”。仅十二日至十五日,被杀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失踪五千余人。失踪者多半是永远失踪了,国共第一合作破裂,近代中国再次进入茫茫黑夜。屠先生——分裂势力中的实干家,以毕生精力把江湖帮会统合成他的暗流王国,曾与红色阵营合作无间,政变中却成为极具组织和改革的刽子手,一时如日中天。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上海街头,车水马龙。
屋塔上一名身负炸弹的红衣少女静静旋转。她神色冷峻地望着街头缓缓驶来的轿车。她知道,里面坐着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右派势力屠系掌门——屠先生。突然她将手中炸弹投向渐渐驶近的轿车,随着爆炸声撕裂宁静的上海,街头巷尾应和般地窜出各路来人展开一系列刺杀屠先生的行动。红衣少女被枪击引发身体上的炸弹爆炸。阿卯挥着锄头冲向轿车,却被人拦截,亦自爆于乱斗之中。 原本只是过路人的芦焱见此忽然激发了心中的正义心和激愤,手持只剩匕尾的匕首冲了过去,然而人刚到车门前这份义愤填膺却转瞬被心智崩溃所取代。屠先生手枪指着芦焱的脑袋,芦焱不管不顾地擎住屠先生的手臂,发了疯似的拿断匕一下又一下地死戳屠先生腹部。刺杀以失败告终,芦焱逃离上海,受伤的屠先生对其恨之入骨、大肆通缉,将其列入追杀榜之首,代号“红先生”。从此,芦焱多次化名,逃亡9年,寻找容身之所。
一九三六年,西北,乌云密布,北风呼啸。
芦焱昏倒在西北荒野中,幸而被附近的村民救醒。喂他喝水的大叔让他赔偿二毛五,只因他跟村民打赌芦焱会死却没想到他活了过来。气息微弱的芦焱并未理会,只询问这里是不是保安。闻言村民们笑话他只说这里是天不管地不管的一棵树。大叔搜了他身子发现他身上没有一分钱,便吆喝着儿子回家不再管他,村民们也纷纷离开了。临走前有位村民问他姓名,他犹豫了半响,答道:“何思齐。”
这天晚上,两个头套麻袋和猪圈的人突然挟持芦焱。芦焱正准备吃毒药自尽,对方却说只是开个玩笑,将芦焱称为同志。芦焱不知是敌是友,只下意识地装傻充愣。然而对方一人却将他的秘密一一道出,说有人托他照顾芦焱,并劝芦焱赶紧回头。因为保安在招纳进步青年,屠先生的人很容易便能装扮成进步青年将他绑架。芦焱却说无所谓,只求“朝达、闻道、夕死”。那人再三劝阻无效,不知是夸还是叹地说了一声“轻狂孟浪”,便将一个小本子交给芦焱,告诉他这本子便是“种子”,保护种子的人也叫“种子”,并声称种子成员组织正式接纳了他,让他老实待在一棵树等听到“惊蛰”就有人来找他。芦焱借口握手将诸葛骡子头上的猪圈和麻袋掀开了。诸葛骡子说此后都由他来管他,叮嘱他拼了命也要保护好种子。芦焱感觉,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
因逮捕红先生不力,屠先生两名部下被发配新疆。而与此同时屠先生的得力助手时光不甘于留在上海签字和发电报,一意孤行地打算身赴非隔离带——两棵树。奉屠先生之命,屠系手下门栓和九富只得紧紧跟随时光。三年后,穿过大沙锅地带,时光带领手下来到了离延安不远的共治区——一棵树。时光对这片之前国民党无人能入的红军苏维埃地区既感新奇又不以为然,因着屠先生送来的共党与日寇作战的武器粗糙至极而不堪一击。意气风发的他准备为屠先生在这块土地上烙上他们的足迹。
留在一棵树的芦焱化身为教书先生正教着小孩子们踢球,这时国民党官派督教巴冬来却数落他的教具粗糙。芦焱谦虚说到自己认得几百个字便滥竽充数一下,巴东来却痛斥他误人子弟、诲人不倦。目不识丁的村民们反而对他不屑一顾。因为他整天高谈阔论,却从不教学。
皖南事变后,屠系势力天目山的双车老大和若水麾下船家的笑面暴以及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人种子成员陈植于一密室秘密商议国共合作的事。屠系势力与若水势力虽只是上海滩的两大势力帮派,却也吃着国民党的官家饭。双车和笑面暴笑称陈植为“拉和老陈”。而陈植也不辜负这个称谓,尽职尽责地从中斡旋,只为劝服两大势力与共军合作一致对抗日寇。屠系与若水本水火不相容,最近却似乎也勾结起来暗中监视共产党。陈植小心应付着笑面下的波涛暗涌,发现他们一致图谋着他手里的”种子“。突然,厅外有人高呼“惊蛰!船家的人!惊蛰!”。随后那人立即被守在室外的啰啰们乱刀砍死,一下失声。陈植看了看眼前面上谈笑风生的两人,冷冷一笑,说惊蛰就意味着我方被崛起了至少十个以上的站点,反问他们是不是要同室操戈等着日寇踏平中国。
第2集:天目船家朝共开火 种子接报启程向沪分集剧情介绍
秘会表面的和谐终于分崩离析,天目山与船家的人正式向共党拔枪开火。陈植吩咐邱宗陵发报明码“惊蛰”,邱宗陵却趁陈植转身之后掏出手枪指着他的脑袋,陈植解开外套纽扣露出绑上身上的手雷,说要死一起死。恰在此时,九宫浴血奋战到门口,被邱宗陵眼疾手快地开枪打中腹部。陈植急忙掩护九宫逃上天台。九宫质疑陈植为何不将他们一网打尽,陈植解释邱宗陵叛变以及缩头缩尾的笑面暴竟敢出头,种种迹象都疑点重重。陈植嘱咐他一定要活着出去,保护好种子并告诉青山,随即将他推下天台。
上海滩忽然间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原本沆瀣一气的双车和笑面暴之间忽然剑拔弩张。陈植正准备返回密室,却发现邱宗陵一脸疲惫地对笑面暴说人都死了。笑面暴怂恿拿到种子的邱宗陵一起去领赏庆功,却被邱宗陵拿枪抵住了腹部。邱宗陵将笑面暴逼迫到天井边随即开枪打死笑面暴与他双双坠下楼层,他对双车高声说船家的人要杀人灭口。这一句话成功点燃了两方势力之间的导火线,双方气势汹汹地意欲开打,却被双车叫停。陈植默默走进密室发出了之前未发出的电报。
正在一棵树行医的医疗队长训斥卞融胡乱派药和注射器。卞融心里委屈,赌气说自己把东西要回来。芦焱安慰着卞融,卞融边哭着说讨厌边抱住了他。
时光与手下们正嘲笑着若水手下高泊飞终于敢离开两棵树了,这时一个手下报告他们截获了共党发来的明码电报“惊蛰”。时光确认电报无误之后,门栓正准备吩咐弟兄们上马出发,时光却交代大家休息,等跟他们一样觊觎“种子”的高泊飞没有进展再开始行动。
邱宗陵原来是屠系深藏在共党中为夺取“种子”而安排的内应“边炮”,他告诉双车笑面暴意欲杀他。双车却说他拿到种子就可以死了,就算死也不能杀笑面暴,以至于现在引发屠先生与若水之间更深层次的冲突。双车怒发冲冠,带着手下来到密室找到陈植,种子却已不知所踪。邱宗陵拉动电台引发了小爆炸,本以为会同归于尽的双车却只是被震得耳朵不好使而已,他气急败坏地命人狠狠地打陈植。邱宗陵晕倒之前说陈植可能正是通缉榜之首的红先生,双车便命人一定要将生死不明的陈植救活过来。后来,他将陈植和邱宗陵双双关入牢中。
诸葛骡子向芦焱解释惊蛰便是我党地下组织被连根崛起的危险信号。在此之前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一次是因为出了重大叛徒,另一次便是因为屠先生。种子便是事先留存的备份以及保护这些备份的人,种子的意义在于防止联络网的中断。而将种子护送到地头让种子生根发芽便是种子成员的任务,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有辱使命。这次被崛起的站点便是芦焱的老家上海。然而芦焱仍是不明白种子为何,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活。可能连种子们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种子。只知道这是个阳谋,种子们都是单线接头。没有事的时候种子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有事的时候便把自己的身子往上填,被戏称为“打兔子”。其实只有一个是真种子,其余的全都是假种子,而只有青山知道这其中的真相。
两棵树本有一个连的中央驻军,却被两伙名为马匪实为暗流的势力占据。一伙是屠系手下时光带领的天外山,另一伙是若水麾下高泊飞的黄沙会 。种子们要穿越三棵树奔赴上海,任重道远。大约因此,骡子笑说种子间见面常说“送死的人来了”。骡子和芦焱等种子们要开始启程了,他们谁都不能知道对方的路线,以免被人在严刑逼供之下出卖。芦焱走之前将拦截孩子们的巴督教痛打一顿,村民们觉得大快人心。
第3集:黄沙会枪打一棵树 天外山劫道大沙锅分集剧情介绍
诸葛骡子说落单的兔子好打,顺便用自己的绳子换走了芦焱身上所谓可以选择死法的宝贝。芦焱心痛就这样失去跟了他十三年的东西,更为迷茫不堪的未来和命运苦闷烦愁。卖酒的小老板送了他一大壶水,村民们和孩子们也都为他的离开而依依不舍。芦焱发誓自己一定会再回来。
随着一声炮响将一棵树的痴傻胖子洋芋擦擦炸死,高泊飞带领着马匪们来到一棵树。芦焱怒吼着要杀死马匪却被同行的人死死摁在马车上。而对此早有防备的一棵树村民和医疗队长点燃准备好的土炮,然而土炮却因早已老化而毫无反应。高泊飞只想着多杀几个人充当种子向上邀功领赏,带着手下烧杀抢劫。随后而来的时光认为高泊飞滥杀无辜只为邀功不合他意,吩咐门栓打掉高泊飞的看马的。此时共产党的军队赶到一棵树,村民们欢呼一棵树有救了。高泊飞只得带着马匪们去追马。巴东花了五块大洋坐上了马车,而芦焱的马车因为驶向方向截然相反的东沟而躲过了时光的搜查。而后时光却发现芦焱中途下了马车往两棵树走去,他带着手下拦下芦焱,门栓说出了芦焱化名为何思齐之后捏造的生平历事。芦焱误以为之前在一棵树滥杀无辜的是时光,冷静清醒地说一定会杀了他。然而时光给了他一把枪他却说自己没种不敢动手。时光说在一棵树喊打喊杀的是黄沙会,而自己只是打的只是黄沙会的马匹。芦焱看出时光说的是真话,道了声谢并说自己只是想落叶归根回到家乡临潼。时光看出芦焱的疑点,却因自信于自己的掌控力将他放行,并让门栓查清芦焱的图谋。随后时光拦截了诸葛骡子的骡车,骡子装傻演戏却没有逃过时光的火眼金睛。骡子说他是受人所托带着三百大洋去赎回高泊飞绑架的古老板,他直觉骡子是种子却因疑惑骡子与高泊飞的关系而免他一死带回刑讯。
双车带着吃的来到牢中,双车直接问陈植是不是红先生。陈植却打了个哈哈,道破双车目前的当务之急,建议双车将邱宗陵作为替死鬼缓解屠系与若水之间的紧张关系。双车对于邱宗陵的作用不以为然,而陈植却暗示邱宗陵游走于三方势力中有可能还与日本人有关。双车知道陈植是个打死撬不开牙门的狠家伙,所以在屠先生发令之前他不会过问种子的下落。